6月24日,一批來自台灣大學、政治大學、清華大學、交通大學、成功大學、中正大學、東華大學、東海大學、實踐大學及世新大學的教授,共40幾位,在立法院的第一會議室,舉行公聽會,反對5年5百億的計劃。為了支持他們,我也準時在9時45分於立法院出現。
幾年下來,參加幾次公聽會的經驗都不是很好,我其實有點厭倦。這次的公聽會一樣如此,仍然是立法委員作秀的場所。雖然到最後,讓教授們暢所欲言,但因為時間顯然不夠,並無法與官員作深入的對談。我看到想講話者眾,最後放棄上場的機會。但發言稿,我還是準備著。
我的發言主要是從幾點,提出針對5年5百億的質疑:
(一)模糊的目標能達到嗎?
追求何種一流?那一種百大?全世界那麼多的大學排比,要追求那一種排比?依照94年4月16日的教育部簡報,所謂一流大學就是:(1)充足經費、適當規模、完整學術領域、充沛的人力與支援、有利國際化之環境及策略。(2)一流教師及待遇、工作環境及保障,傑出的研究、充分的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,先進的設備及優異表現的學生。這樣的一流,大部份大學都可以競逐,何以只選定兩、三所?
(二)綁標式的政策恰當嗎?
還沒開始比賽,誰會勝出已先放出風聲,這如何讓人心服?這種綁標式的政策,已讓其他學校自認是棄兒。縱然教育部最近發函調查,但大部份學校認知教育部早有腹案,不是自我排除,就是抱著試看看的心態。這種綁標進而造成棄兒式的政策,恰當嗎?
(三)其他學校不值得重點補助嗎?
不少國立大學及私立大學早就發展出各自特色的重點領域,卻不見教育部主動點名式的重點補助,對照前面兩、三所早已「欽點」的大學,這難道是一種合理的政策?讓已各有特色及重點的學校,發展世界一流的領域比較有可能?還是要求兩、三個大學得到整體一流比較有可能?教育部應該衡量一下。
(四)炒短線的作法可行嗎?
5 到 10 年就想要成就一流,那有這樣子炒短線的作法?我們炒短線的資訊產業,只發展出代工式的一流,現在則已落入夕陽境地,難道我們的教育還要再玩一次?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,已向西方求學了一百多年,還不斷在留學(流血)!一百多年都無法解決的事,如何期望5到10年可以達到?
(五)百大又能代表什麼?
將 5 百億集中,就能保證進入百大嗎?如果達不到,錢已花光了,誰該負責?這些學校真強到所有學門都可獨霑這些經費嗎?若一定要這麼作,請政府給大家可以接受的解釋。大學排名一向是商業機構的把戲,學術圈本身的健全發展,自有一套同儕評估方式的認可制度,我們的政府不如此之圖,卻獨鍾大學是否進入百大,到底是要爭什麼?
(六)後果有考慮嗎?
二桃殺三士還算輕微,比較嚴重的後果反而是「兩個一流,數十個不入流,加上一百多個沉淪」。只為了一個虛無飄渺的百大名號,要讓其他一百多所大學遍地哀號,這算是那一種政府?父母親為了栽培一個小孩,讓別的小孩犧牲,是台灣貧窮農村時期的悲哀!沒想到,經濟如此發展的台灣,卻還在玩這種殘酷的遊戲,孰能忍之!
(七)難道沒有更根本的問題要關懷?
教育部到底知不知道,現在的大學生學習動機的低落已到何種程度?大學部的老師,現在已陷入水深火熱之中,不只要具備補習班老師的口才,還要有演員的身段,才能吸引住這些學生稍帶關懷的眼神。這一些學生再不救,台灣的未來才真正可悲。這種問題直接與中小學的養成教育有關,如果不能在中小學打好基礎,如何期望台灣的前途無量?就靠一、兩所大學打入一百大?難道台灣的未來就是這一、兩所大學的學生所繫?一將功成,台灣恐早已沉淪矣。
幾天前,一個博士班的學生,傳了一份一位媽媽將 9 歲小孩帶到美國讀書的故事(註),媽媽最後的心得是:「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,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海洋,他們要讓孩子知道,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;他們沒有讓孩子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,但是,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怎樣去思考問題,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;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,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一切努力,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,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作慾望和嘗試。」這樣的教育,才是教育部該試圖達成的目標。教育部應該好好想想百年規劃所需的教育基礎建設是什麼,競爭似的只圖兩、三所大學的一流,不願面對及解決台灣的教育問題,台灣的未來在那裡,確實令人擔憂。
註:題為「當我把九歲的兒子帶到美國」,原載於美國中文在線論壇(http://bbs.tycool.com),欲詳全文可至新華網 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overseas/2004-11/10/content_2198330.htm。
星期三, 6月 15, 2005
殘酷的退學率
 教育部公佈大學退學率,隱含著退學率愈高,大學品質愈好的想像。這樣的思維,後面隱藏著多半人看不到的不意圖後果;因為以退學率衡量辦學績效的作法,會讓學生失去改過自新的機會。
教育部公佈大學退學率,隱含著退學率愈高,大學品質愈好的想像。這樣的思維,後面隱藏著多半人看不到的不意圖後果;因為以退學率衡量辦學績效的作法,會讓學生失去改過自新的機會。一個初入大學的新生,常常還在摸索階段,第一個學期更是最好玩的時期。如果只因一次失足,就將他逐出學校,會不會太過殘酷?會自省的學生,摔了一次,會幡然省悟,回頭加倍用功,可能走出一條坦蕩的未來。不會反省的學生,會犯第二次的可能性很高,此時加以退學,當然是疚由自取,不值得原諒。
世新去年才將單二一制度,改為雙二一制度,即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考慮。我當教務長才兩年,碰到懊悔的學生不知有多少,其中主要的都是一時不察,產生無法挽救的後果。
教育部當前如此強調退學率的思維,很可能會造成各校為求表現,努力當掉學生,以提高二一制度退學的比率。請問,這樣的不意圖後果,會不會讓學生連反省及翻身的機會都沒有? 我曾與本校傳播學院成露茜院長就此事進行交談。成院長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書多年,對美國的教育系統知之甚詳。她告訴我,美國大學學生知難而退自行休學的比例一向大於被退學,換句話說,學生如果自己覺得興趣不合,或是課業無法勝任時,學生自然會知難而退,不用等到學校下最後通牒。
成院長事後傳了一份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資料給我,在這份文件中,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生如果 GPA 在 1.5 以下會被退學。1.5?1.99 則進入觀察期,如果兩個學期內未通過觀察期(GPA 2.0),才會被退學。這樣的制度,保留了很多彈性,讓學生有補救的機會。
對照台灣,我們的大學傾向於一次二一(半數學分數未過)即退學。現在有些學校開始採行雙二一制度,卻可能造成退學率下降的趨勢,而讓教育部貼上標籤,被視為辦學不力。但何者較具人性,其實有待深思。
教育部在這整個退學率的政策上有待斟酌之處不少,不加思索,冒然推行,對學生的未來實在有欠交待。一試定江山,被批評為阻礙學生學習的多元機會。但過度重視退學率,讓學生失去補救的可能,又該當如何說?
更根本的解決辦法,還在於學生心態的建立。高中生對大學的認知不清,將大學視為解放壓力的地方,常常將寶貴的一、二年級時間浪費掉,等到想回頭時,又已為時已晚。也許,高中應該承擔起部份責任,高中教師應該教育學生對大學有正確的認識,讓學生了解大學是另一個學習階段的開始。要讓他們知道,花那麼多錢及時間「由你玩四年」,是一種自我的沉淪。
大學則有必要針對當前的新生,進行大學宗旨的認知培養。讓大學生儘早建立自我學習的態度,早日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。其實,這也是世新大學為什麼要推出「新鮮人守護神」的主要原因;如果不從大一開始進行調整,其後的二、三、四年級,對所有老師都會是極大的挑戰。
GPA,grade point average,學業成績總平均的縮寫。
計算方式:1.將分數(0?100),換成等級(A?D,4?1點)。2.計算學分總和及等級點數(學分乘以等級)總和。3.等級點數總和除以學分總和等於GPA。
分數式換成等級的標準,一般公認是:A:80 分以上,4 點B:70?79 分,3 點C:60?69 分,2 點D:50?59 分,1 點50 分以下不計算學分。
星期三, 6月 08, 2005
印順導師一面緣
我會接觸印順導師的作品,與李元松的介紹有關係。那一年,亡妻得重病過逝後,我一力探尋佛法。亡妻留下的李元松作品,變成我追求劇變後的精神慰藉。從李元松的簡短自傳中,他特別提及,民國68年軍中退伍,接觸印順導師的《妙雲集》,是促成他轉攻中觀哲學的主要關鍵。
我一向對李元松極為佩服,他這一段自述與《妙雲集》的關係,讓我對印順導師的作品開始產生興趣。那幾年,除了《妙雲集》只買了幾本外,印順導師的作品我多半全都有,包 括《空之探究》、《中國禪宗史》、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、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及《印度佛教史》等。
看了印順導師的書,方知道從理性的角度探觸佛法不是不可行。我就是看了印順導師的書,才解答美國讀書時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。在美國時,我曾問過佛學社的同學──一個在南亞系研究佛教的博士生,為什麼佛教起於印度,卻在印度沒落?我並沒有得到我要的答案,直到看了印順導師的書,才了解佛教在印度衰落,與佛教的性力派的興起有關。這樣的答案,如果不是透過學術的角度,不可能會有此解說的。
讀了他的書,心雖嚮往之,但卻無緣見面。事實上,也沒有多少人知道印順導師在那裡。
他的晚年,處於潛修狀態,常常在新竹的福嚴精舍、嘉義的妙雲蘭若及花蓮的靜思精舍間游動。不認識的人,想看到他非常不簡單。
很巧的是,大約10年前,我與中華佛研所的杜正明老師,正在幫台灣大學哲學系的釋恆清法師建置佛學文獻資料庫。當時,佛學資料庫有計劃地在進行經典數位化的工作,其中當然包括印順導師的《妙雲集》。但一套《妙雲集》20餘冊,幾百萬字,以佛學文獻資料庫的人力實在無法勝任。
其實,當時有些佛寺已自主地找義工,一個字一個字將《妙雲集》敲成數位檔。如何說服這些機構一起合作,願意將辛苦成果捐出來,製作成數位資料庫供大眾使用,是當時思考的主要問題。另一個問題則是版權的問題,這必須找印順導師授權才有可能。因此,為了此事,恆清法師連絡了《妙雲集》的出版者法藏法師,找到了印順導師,並約好了時間, 要到南投尋求他的同意,簽署授權書。
1995 年 9 月 12 日那一天,我們一行四人,開車直奔法藏法師在南投鹿谷的精舍,印順導師夏天最喜歡的修行場所。那是一個很幽靜的清修場所,全部由竹子所建造成的矮小房舍。
我們大概早到了,印順導師還在休息,我們就在前面的待客室等印順導師準備好,才上樓見他。我已忘記印順導師當天講了什麼話,我只知道,他精神還好,話並不多。我們跟他頂禮,簽完授權書,合影後,沒有多久就離開了。
隨後,我就沒有再見到他。間而佛學資料庫的義工韻如,告訴我《平凡的一生》這一本傳記,讓我對導師的了解更深一層,也才知道他曾受過白色恐怖的經歷。為了謝謝我對佛學資料庫的義務幫忙,釋恆清法師知道我對印順導師的崇敬,還買了一套《法雲集》,由韻如轉贈給我。
如今,導師走了,套書卻仍在。看到種種追思在醞釀,我知道我必須認真重看導師的作品了。我已耽於俗事太久,應該是回頭重尋真諦的時候了。
星期三, 6月 01, 2005
圖書館員的侷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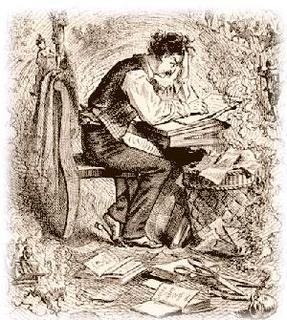
帶著讀書會讀了幾年西方經典以來,我慢慢發覺圖書館員的侷限。
閱讀是一個很細緻的行為,面對原典,必須推敲每個字每個段落,偉大思想家想要說出的話。然而,有些思想家的思路就是不一樣,有時更會創造出一些新概念,讓讀者常常如墮入五里霧中。
因此面對原典,不只需要有不同版本,更需要好的譯本,而圍繞這些原典及譯本,更需要解讀的書籍,幫著讀者走進原典的世界。解讀的書籍,通常以譯者的讀本會最好。
除了導讀的書籍,有時還需要思想家的傳記及思想介紹,透過對思想家的了解,幫助走入經典的世界。另外,圍繞著經典,還有更多針對原典的介紹及評論的書刊,更是必須的輔助材料。
然而,更大的挑戰,還在於思想家在原典篇頁中,偶而流露出的抽象概念。如果沒有弄懂,就會像失去方向的車子,不知會開向何方。為了弄懂這些抽象概念,通常需要哲學辭典、各專門學科的百科全書,更重要的則是,必須檢索各種資料庫,看能否找到學者針對這些概念的專文介紹,一點一滴地破解作者的語意迷宮。
讀康德的《純粹理性批判》就是一個例子。這本書有三、四種譯本,我們幾乎都買了,看了看,挑中了韋卓民的譯本。為了瞭解康德的抽象思維,我們也收集了韋卓民等人的導讀本作為參考。
但其中最有幫助的,反而是大陸學者李澤厚的《批判哲學的批判》,這本書基本是康德思想的總體介紹,對閱讀康德的書有極大的幫助。然而,甚至這本書都不是那麼好懂,因此,常常就在原典與譯本中來回穿梭,目的只是想徹底了解康德在說什麼。
這樣的情景,在讀 Gadamer 的《真理與方法》時同樣出現。為了讀這本詮識學的經典,我們找了唯一的洪漢鼎的中文譯本。有了中文譯本,仍很難走入經典的世界。不知怎麼搞的,這些哲學家的寫作,總是一點都不乾脆,思路繞來繞去,有時硬是無法區分,到底是作者在說話,還是被引的思想家在說話。最後,只好求助於洪漢鼎的導讀本《理解的真理》這一本書,幫忙走進作者的世界。
但因為 Gadamer 引入的思想家太多了,常常必須先行處理被引思想家的概念,才能逐步推進。例如《真理與方法》中的第一部份,探討美學時,康德的思想就出現不少,以「合目的性」這一個名詞來說,就須上資料庫、上網,甚至翻閱朱光潛的《西方美學史》,從中找尋解譯的蛛絲馬跡。
最大的挑戰,還在於讀 Scott Lash 的《Critique of Information》時出現的問題。這本書沒有譯本,偏偏裡面出現的思想家個個有來頭,例如拉圖爾(Bruno Latour)、麥克魯漢(Mar-shall McLuhan)、拉菲弗爾(Henri Lefebvre)、列維那斯(Emmanuel Lev-inas)、Paul Virilio、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)、海德格(Martin Heideg-ger)都是主要對話對象,除此之外,被作者拉進來陪襯的還有哈伯馬斯、胡賽爾、馬克斯、阿德諾、拉康及Harold Garfinkel等人。
處理一個已經不得了,更何況出現這麼多思想各異的思想家。也因此,這一本書我與博士班的學生讀了已至少 四遍,但仍不敢說完全理解。其中最難處理的就是繁複的抽象概念,例如提到馬克斯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,就必須回頭了解馬克斯的思想。為了了解拉圖爾的非人(non-hu-man)及擬客體(quasi-object),就必須回頭尋找拉圖爾的作品。
而為了掌握班雅明在書中的位置,必須重讀班雅明《說故事的人》。為了理解麥克魯漢,必須閱讀他的《認識媒介文化》。為了知道拉菲弗爾的空間實踐概念,翻尋的譯文及介紹性作品更不知繁幾。為了了解 Tonnies 的 Erfahrung 及 Erlebnis 這二個概念,不知推敲了多久,最後還是透過百科全書才得知堂奧。
其中,列維那斯(Emmanuel Lev-inas)給我們的挫折最大。為了試圖理解他的思想,我們必須上大陸的哲學網站查尋任何有關他的思想介紹,我們更試圖蒐集任何專書及期刊中,有關他的作品的譯本及介紹。那一些哲學史、那一種期刊有他的思想介紹及譯文,不敢說完整,但我們都已初步掌握。而這些書及期刊,保證台灣有收藏的少之又少。就是中國期刊網,也照樣查不到。
從上面的描述,可以發覺有生命的思想世界,像是一個磁場或是太陽系一樣,以原典為中心,週遭圍繞著眾聲喧嘩的不同文本,包括譯本、解讀本,介紹、評論、字典、百科全書、論文。它是一個思想的綜合體,以思想家為經緯,全部串在一起。
在這閱讀的過程中,對我們最大的挑戰,在於如何掌握完整的各種文本,幫助我們打開經典內藏的謎團。很可惜的是,圖書館當前的蒐藏,常常是掛一漏萬;圖書館所收藏的書刊,也好像獨立的個別單子,缺乏以原典為核心的文本串連方式。因此,對讀者的深入閱讀常常幫助不大。
圖書館員一直在談知識加值,其實所做的並不多。以前圖書館員曾試圖編製各種索引及書目,幫助學者找尋資料。但這樣的勞力工作,因為全文資料庫及網路蒐尋的出現,已經榮光不再。但後者的工作真的不重要嗎﹖由上述所描述的閱讀循環過程﹐其實又不盡然。
其實﹐圖書館員如果能確實瞭解以原典為中心的文獻分佈﹐進行意義之網的文本蒐集與編整工作﹐應該比較會得到深讀的讀者的肯定。也許﹐每一個圖書館員都應該讀一本經典看看吧﹗讀完後﹐就會知道我所說的意思了。
訂閱:
文章 (Atom)

